“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这句耳闻能详的话出自《庄子·逍遥游》。它作为《庄子》首篇,是可以独立成篇的大文本,是透视《庄子》的正法眼藏,是永远可以讨论永远也不会结束的话题。如:道家与神话、有用与大用、游化主体、有待与无待、道家与语言、小大之辩、逍遥与秩序……这些话题的讨论历久弥新,随着时代的变迁,认知主体的不断更新,经典与诠释的方法让今人与古人共聚一堂,在《逍遥游》衍变的大剧场中,天籁与人籁共同谱写出“渊默而雷声”的庄乐。

因缘于此,2017年11月4日、5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经典与诠释研究中心、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共同举办首届了两岸关于《逍遥游》的文本、结构与思想的盛大会议,本次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5303举行,出席本次会议的有60多位学者和博士研究生,现场盛况空前。本次活动也是上海市社联第十一届(2017年)“学会学术活动月”的活动之一,得到了社联的大力支持。

“庄子的升天神话”
《庄子·天下》篇对古之道术进行了批判和终结,作的是某种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台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著名学者杨儒宾教授从诸子的起源入手,分析了诸子的三个起源:一是为了“救世之弊”;二是追溯到上古的王官之学,私学出自官学;三是庄子主张天下学术都是由“太一”所化。前两点太经验化,不足解释道家的心性论和形上学的深刻性。因此,要追溯“太一”的文化内涵,很容易想到原始宗教,也可以说是原始版的哲学。从神话到哲学是各大文明的相似之处。道家神话可以归结为老子的大母神话、黄帝的天子神话和庄子的升天神话。每种神话所代表的精神层次是不同的,而庄子的升天神话强调从深层意识的自我同一中走出,主体参与气化的流行。这样的视角可以说为我们打开了逍遥游的神话之门。同时,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李志恒指出将道作二元论、形上学式的解读方式可以追溯到道家哲学与神话原始宗教的渊源关系,他尝试从“境识缘构”的角度解释变化之“道”,取消道的形上学性质且保持它的超越性。

“有用与大用”
有用与无用的话题源自庄子与惠施的一个争论,然而庄子在承认无用之大用时,却提出了一个反例,不会鸣的大雁反而被杀,这里面似乎蕴含悖论。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方万全教授以分析哲学的方式阐发了这个论题,并指出关于“有用与大用”的争论,有两个不同路线的发展:一个意在彰显庄子的无用之为用的看法,另外一个则彰显了庄子意在指出超脱无用与有用之争的必要性。后面这点也指向了“大而无用”的大用,指的可能是什么。在上述悖论中,显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一物有用不必然害其生,而其无用也不会必然能全其生。更为重要的是,庄子告诉了我们一个没有“材与不材之间”之做法的缺点,而能让我们全生的方法,即“乘道德而浮游”的方法,这才是庄子的大用,从而达到“乘道德而浮游”的逍遥境界。
“大”与逍遥有什么关系呢?“大”可以作为逍遥的底蕴吗?长江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方勇教授指出清代治庄者对逍遥义的阐释是以“大”为逍遥的大合唱,批评了他们用儒家的“鸢飞鱼跃”、“活泼泼”、天理流行等观念来阐释《逍遥游》。关于“无用”的话题,德国籍、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何乏笔教授受到海德格尔在虚构的交谈中用“无用”来回应德国战败的困苦的启发,对卫礼贤翻译的“无用”产生质疑,他主张用(Gebrauch/use/usage)取代主流的翻译,更能表达逍遥与无用的关系,阐明庄子无用思想的不同层次,突出“用无用”的吊诡性。

“游化主体”
逍遥的主体是谁?主体是固定的还是流动的?世界的瞬息万变,主体应接不暇,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把捉世界的流变,唯有我们与化为体,在化的缘境中我们也就物我两相忘了。台湾中山大学特聘教授赖锡三教授认为主体是流动的,万物也是流动的,因为世界彻彻底底就是流动的,人与万物都不能外于这一气化流行的大化世界。逍遥这种既游且化的主体具体在物我关系和人我关系中展现,是自然美学和人文治疗结合的产物,既在关系中自由,又丰富了自由的关系。只有出入内外之间“无所住”,以保持动态往来、两行转化的“非同一性”之吊诡性修养方式,才能真正游化于天地之间。
道体的呈现是相对主体来说的,不同的主体所窥见的道体是不同,然而道体总是局部地呈现,因此主体的层次决定了道体呈现的层次。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对《逍遥游》的文本进行了解构,呈现了道体在自然世界和人间社会的层级展现,并对肩吾、连叔、接舆境界层次作了分析,得出了神人即圣人的结论,尧与神人是二而一的关系。接舆的真正内涵是接孔子之舆车的圣人,这就意味着逍遥的主体不仅仅是一种生命状态,而且还应该将“逍遥”推延到社会政治的场域之内,为人间社会提供药方。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刘沧龙教授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外在他者”对人们构成的局限。面对这种局限,只有透过自我转化的功夫,才能让有待之身成为逍遥之场。庄子的“心斋”功夫便是此一视角转化的技艺,使得“外在他者”调转成自我理解的内在条件,成为“内在他者”。针对毕莱德的“我身主体”和杨儒宾的“游之主体”,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柯小刚教授提出“气化主体”,他的依据是“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气”即非片面属身,亦非片面属心,它是身心之间的“虚而待物”。“虚”是人与物之间的“待”。气化主体需要做“兼体而无累”的功夫,在“之间”浮游,才能打开逍遥的境界。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郭美华教授认为主体应该不断地自我否定,这种对自我的领悟方式,使得主体从流俗世界中解放出来并回到自身,“从有限性走向整体性”。个体领悟自身的有限性并自觉持守在自身的界限之内,让“他者”来临,与自身共同构成二者共存的“整体性境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文江教授对“四子”(许由、啮缺、王倪、被衣)这一师生组合出场次数做了细致的分析,发现“四子”的隐、显是有深意的,出场次数越少主体的境界层次越高,侧面反映了道家风范和独特的修炼方式。

“有待与无待”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鹏图南、宋荣子定乎内外之分、列子御风而行,依然有所依赖,至于无所待的境界只有至人才能到达。长江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林合教授从分析哲学的角度构建了现象界和本体界,本体界是至人所处的世界,但处于两个世界中的主体是同一的。他认为至人的本质特征是“无己”,即没有自我观念,进而也不会有外物的观念,因此他根本不会区别物我内外,进而也不会区分彼此,更不会区别美丑、善恶、是非、大小、贫富、穷达等等。这样,他当然能够做到“无功”、“无名”。当一个经验主体(身心统一的主体)随着成心的形成也就越来越远离了道,只有通过“心斋”的方式,才能无己,无己便能安命,安命即意味着体道,体道便能逍遥。逍遥不仅仅作为心灵的境界,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状态。
同样具有分析哲学背景的台湾阳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郑凯元教授从时间、空间与转换的新颖观点来解读《逍遥游》,他采用莱布尼茨的时空观为分析思路,发现在《庄子》里也有类似的时空观。时间可以分为三种:认知性时间(概念化的时间)、经验性时间(主观感受的时间)、实在性时间(以道为本的时间)。至于空间,他认为道的空间超越日常的物理空间,“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针对“有待与无待”的问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邓联合教授另辟蹊径从郭象的视角区分了“有待逍遥”与“无待逍遥”。“有待逍遥”仍非究竟,因为在有待的境界中,物有大小、死生,物皆拘于“一方”,“物各有性”。而“无待逍遥”作为一种生命形态,其特点是:一此中圣人能够游于“无小无大”;二圣人与“化”同体,能够“齐死生”;三圣人与万物“冥”,而不拘“一方”。

道家与语言
庄子的语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天下篇》自叙其语言特点曰:“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沿着语文学到哲学的分析进路,突出“卮言”的特色深入开掘逍遥之义,分析了“逍遥”即“消摇,“鲲鹏”、“昆仑”、“空同”等卮言的含义,总结出“卮言”的本质不在于夸饰与修辞,而在于突破语言的固著性、激发语言的魔幻力,以此提示道家哲学之幽眇玄理。“卮言”是一种超乎日常语言的哲学语言,尤其是提示精神境界的“元语言”(meta-linguistics)。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从“寓言”角度诠释《逍遥游》与以“卮言”诠释逍遥义形成大合唱。他认为郭象注《庄子》历经两种路径,一是《庄子》“寓言十九”,故需要从“寄言出意”到“忘言寻旨”;二是郭象以“后经学”态度对待经典,即述即作。以“足性”释“逍遥”,实际上已经在经典解释的过程中实施哲学话语的创新。支遁举出桀纣的反例,主张用“至足”超越“自足”,自性本空,“至足”才是真正的逍遥义。但是,不要忘记寓言有现、隐二重义,庄子寄言以出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正言若反”,因此经典诠释不能忽略文本本身的语言。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系李智福博士把屈原拉入庄子的视角,并对两者的逍遥做出辩证对比,他认为庄子的逍遥是哲学式的逍遥,诉诸普遍追求;屈子作为诗人是诗人式的逍遥,实是个体体验。普世追求的哲学式“逍遥”与境域性的诗人式“逍遥”构成一种内在张力,并最终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的“庄骚”古典传统。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蔡岳璋认为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他以文学表现与思想表达之间的共生运动与认识关系为主题,探索它们在《逍遥游》的基本蕴含方式,重新检视庄子文学如何内含于自身思想的总体表现。

“小大之辩”
《逍遥游》篇最先出场的辩论是小大之辩,台湾大学哲学系林明照教授就是从此辩入手,他认为《逍遥游》中的小大之辩,不是在第一序的大、小之別下,透过“小”与“大”的区别来展现其价值区别。而是在第二序的反思意义下,以“大”为参照背景下的“小”,来提点第一人立场的特质及局限。此中的第一人立场,蕴含著名制的规范力,以及由之预期的有用之功。小大之辩在《逍遥游》中,正是在第二序的反思、破坏及超越意义中,呼应了“三无”(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遙向度。而无用之大用,也正是从“三无”中展现出的“大功”与“大用”。无独有偶,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王玉彬副教授也对庄子“大小之辩”做了新探味,他认为自是为小、自化为大,这里蕴含着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存决断——在“自大”中变“小”,还是在自“小”中变“大”。因此,庄子所谓“逍遥”,便非某种既定的价值标准或至极的精神境界,而是以天道为价值根源,以“小大之辩”为生存决断、以“化-通”为存在方式的活化生命和生命活化。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贾学鸿教授由“小大之辩”看《庄子》的认知逻辑,她认为人们观念世界中的“小大之辩”具有主观性,只有放弃主观层面的小大之辩,转向非逻辑认知,在七维空间中流转、跳跃,从而实现“不言而言”的语言表达,才能逍遥。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康宁以“环中”释逍遥,他认为“大”与“小”代表两种不同的视域、两种不同的认知形态,并提出了第三种(超越二元对立,不落两端)的“环中”形态,以“环中”形态来规避小大之辩、有用与无用的问题,呈现游于“之间”的逍遥。

逍遥与秩序
纵观世界历史,历史的车轮总是在有序——无序——有序中匍匐进行,在某种意义上,天道代表着自然和社会的秩序。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否有共通之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陈志伟教授认为有“己”才谈得上具体之用,从而能产生功用和利害观念,将人引入“有待”的各类限制之中,因此庄子希望削除一“己”之私,以至“无己”,而进入“无待”的逍遥。“无己”是“无用”的基本前提,“无己”开启的“无用”是庄子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的独特言辞,通过尧与许由对待天下和治天下的态度,并最终由无为逍遥的道体意象将个体的自适其适和天下秩序呈现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郑随心通过对“姑射山神人”章的分析,区别了两种政治原则:一是以肩吾为代表的“以力为宗”的治天下原则,结果必然导致“天下”成为“理念”的附庸;二是以“神人”为代表的“以化为宗”的成天下原则,象征一种退出型的政治模式,所构建的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深层次的是对自发形成的自然秩序的肯定。两种不同的治道关系并非截然对立,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为前者指定终极方向。西北政法大学哲学系张磊老师对逍遥与秩序作了形上学的思考,他认为作为理想生命的“逍遥”,以破除有封的存在形态为要义,以“道”为根据,以“本真之性”的解放为内容。在超越现实既成规范或制度束缚背后,以“道”的整体性为视域,强调超越分与杂,而表现出对统一于有序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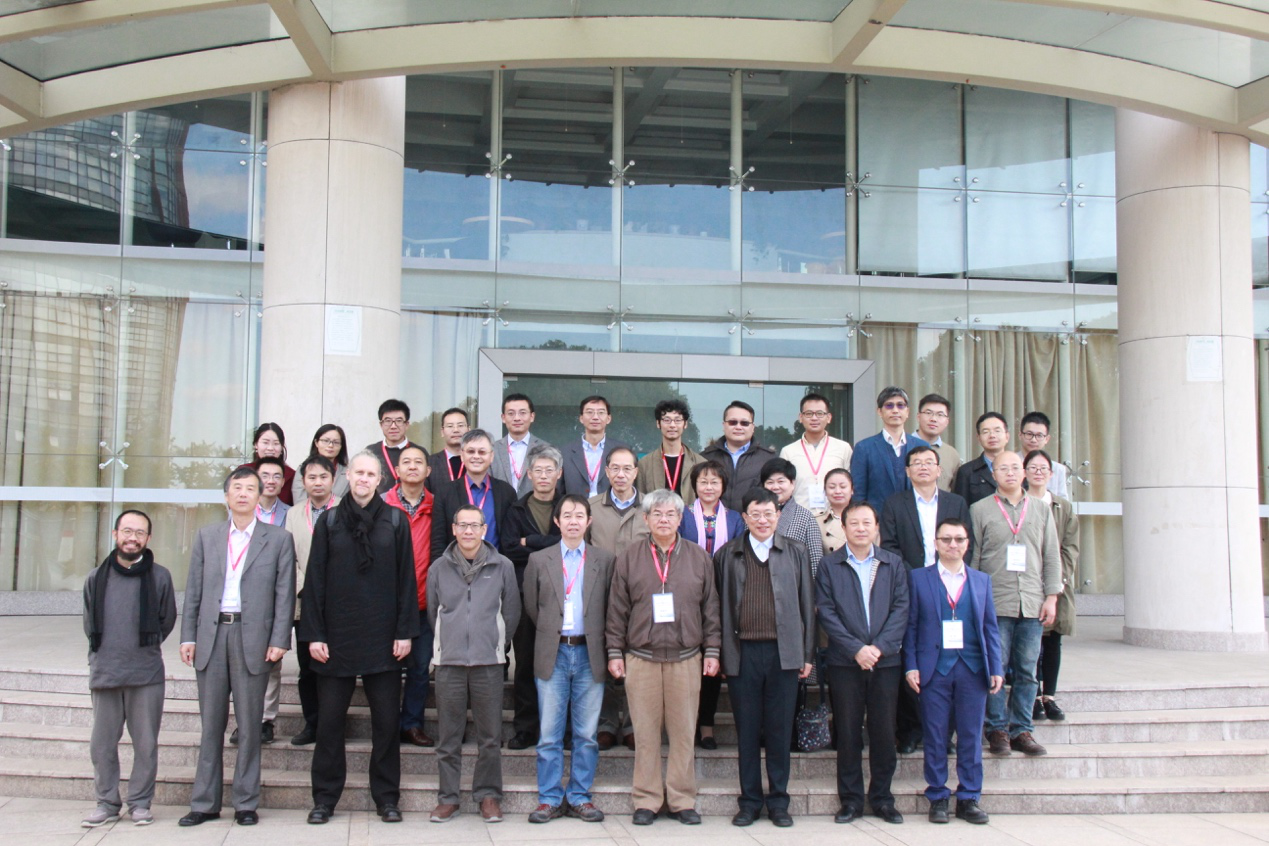
2017年11月5日18点25分,本次会议在圆桌讨论中结束,为历史划上了厚重的一笔。然而,关于《庄子》的讨论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本次会议为《庄子》其他篇目的展开打开了一个空间,希望这样的会议能够继续下去,以便让庄子思想在现代的场域中尽情展开,获得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