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3日晚,应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邀请,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博士陈斯一老师为外语学院师生做了主题为“《伊利亚特》的悲剧诗学”的讲座。本次讲座系“古希腊文学与思想史”系列讲座第4讲,由英语系罗峰副教授主持,逾300名校内外师生以腾讯会议和B站的方式线上参与。
陈斯一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伦理学、政治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思想,著有《从政治到哲学的运动:<尼各马可伦理学>解读》《荷马史诗与英雄悲剧》《存在与试探: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发表中英文论文30余篇。
罗峰老师提到,在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以其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和荡气回肠的英雄壮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按照一般看法,荷马创作的是史诗。但的确也不断有人(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荷马称为悲剧大师,甚至称之为悲剧诗人的老师。那么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荷马史诗为悲剧,荷马史诗中又蕴含了怎样的悲剧诗学?陈斯一老师是目前国内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的新锐学者,他开阔的视野以及对思想史脉络的清晰把握将带领我们深入探讨《伊利亚特》的悲剧诗学。

讲座伊始,陈老师简要介绍了本次讲座的思路:讲座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尼采的悲剧哲学出发,以古希腊艺术史为佐,基于对《伊利亚特》情节与结构的分析,阐述这部史诗的悲剧精神和诗学技艺。
陈老师首先指出,亚里士多德和尼采的诗学视角可谓一古一今,对悲剧做出了哲学性的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提出了一个经典理论,即所谓的模仿(mimesis)与净化(catharsis)的学说。他认为悲剧是最完美的诗歌,因之是一种具有净化功能的模仿。悲剧对于人的恐惧和怜悯有调节作用,通过首先激发这两种人类情感,再经悲剧的艺术模仿将之全部宣泄。但同时,我们又明确认识到这不是真实的,而是艺术的升华。这种距离感可以实现灵魂的情感调和。在此意义上,模仿和净化相结合,实现了悲剧对于灵魂的塑造。
陈斯一老师认为,某种意义上讲,尼采对古希腊悲剧精神的哲学性解释呼应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尼采提出一个著名学说:悲剧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张力性结合,日神精神代表阿波罗的理性和秩序,酒神精神则代表激情和混沌与自然的无常,以及自然对一切个体性差异的消弥。回到亚里士多德,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尼采的学说:酒神实际上意味着悲剧的剧情和内容,包括主人公的挣扎、人生的无常、死亡和痛苦。陈老师表示,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的形式结构都十分精巧。显然,《伊利亚特》的形式结构精妙无比。卷次和故事之间的对称展现了一种古典般的平衡与美学的设计。这其实就是日神精神。《伊利亚特》的形式和内容就反映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张力。这种张力恰恰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和净化的结合。但这并不十分契合尼采本人的说法。尼采认为荷马史诗体现了纯粹的日神精神,到抒情诗和悲剧才有酒神精神。陈老师表示认同尼采的框架和思路,但他认为荷马史诗本身就包含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是十足的悲剧。为了更具象地理解这点,我们有必要进入史诗本身及其背后的艺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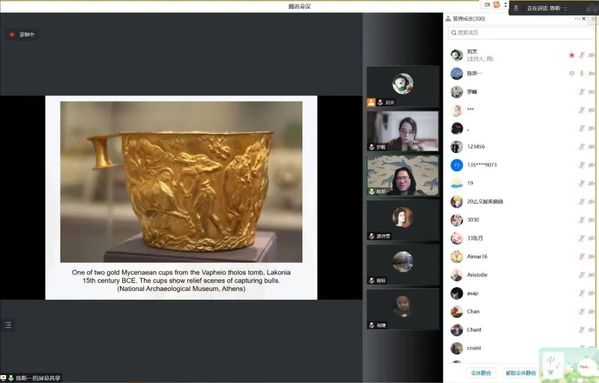
陈老师接着阐述了古希腊历史与诗歌的关系。古希腊历史大体分为迈锡尼时代、黑暗时代、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四个时期。迈锡尼时代是远古的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文明是更为古老的希腊文明,末期还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公元前11世纪迈锡尼文明覆灭,随之进入黑暗时代。因其文字失传,仅留口头语言,口头诗歌由此形成,人们通过背诵诗歌来传颂英雄事迹。直到古风时期才有了成型的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其实是在漫长的口头诗歌传统基础之上加以改编和定型,从而呈现出如今可见的极为精巧的形式样貌。最后是我们最熟悉的古典时代,亦即城邦时代。古典时代虽短暂,却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高潮。
通过扼要梳理古希腊文明与文化的历史分期,陈老师强调了荷马史诗背后的概念基础。作为英雄史诗,《伊利亚特》歌颂的是战争,其中包含着从战争到诗歌的转化。黑暗时代以诗歌的方式传承迈锡尼时代的战争精神及其背后隐含的一个个战斗民族自身的精神追求。这种转化其实反映了自然(physis)和文化(nomos)的关系。因为古希腊人眼中的战争是自然而然的现象,斗争是人生最底层的逻辑。人必须面对苦难和死亡,而文化赋予自然的精神性产品就是诗歌。具体而言,诗歌的生成有一个从诗系(epic cycle)到史诗(epic poem)的转化。区别在于,诗系往往平铺直叙或碎片化,史诗却把这些故事统合一体并进行戏剧化处理。
陈斯一老师指出,《伊利亚特》的剧情只讲述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的最后一个多月所发生之事,却正是通过时间上的聚焦折射整个参战群体。而这种创作过程就是哲学家口中的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古希腊文的“poiesis”就是“诗歌”或“创作诗歌”动词的名词化,广义上指制作某个东西。只不过诗歌用的材料来自于自然和战争的事实。从几何艺术到阿提卡陶瓶,雅典艺术达到了高峰。而诗歌艺术的发展与视觉艺术是同步的,两者精神相契。从时间线看,《伊利亚特》的形式结构也呈现出对称的布局,最终旨在烘托第九卷的一个中心的夜晚。阿基琉斯的拒绝是整个故事的中心转折点,呼应了荷马对英雄史诗母题的根本改编。阿基琉斯的拒绝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升华。他不再关注被剥夺的荣誉和战利品,转而开始思考更为深刻的东西,比如生和死。最后朋友为他而死,阿基琉斯为友复仇,最终才与敌人和解。陈老师认为,这样一种对称的设计不可能是口头无意识的结果,肯定有一位诗人进行了某种编排或改编。而荷马就完成了这项工作。
而作为一种精巧模仿的阿波罗的形式,如何与狄俄尼索斯的内容相结合,完成对苦难和死亡的净化呢?陈斯一老师进而引领我们进入《伊利亚特》的文本肌理。陈老师指出,《伊利亚特》中编排的故事其实均关于死亡。荷马多次用非常诗化的笔调描述了死亡。比如,他把战士的死比作诗歌,把尸体比作被工匠做成战车的一颗树。如此一来,诗人成了制作的工匠。而诗歌本就有“制作”之意,就是把质料做成形式。由此可见,古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诗歌是一种制作。此外,陈老师援引纳吉的观点指出,“荷马”的词根就是“木匠”,意为组装者或木匠将木材组装成某样东西。英雄史诗的质料是死亡,形式是诗歌,它的“死亡”质料需要一定的组装。
陈斯一老师进一步深入谈及荷马史诗的核心主题:死亡。他认为,《伊利亚特》无疑是一首关于死亡的诗,死亡是它的核心问题。全诗240多处对战士之死的描写,战斗描写一笔带过,死亡描写浓墨重彩。英雄要么轻伤或死亡,没有重伤,更没有残疾,没有来世、至福之岛和不朽——死亡是终极的。唯一的不朽是荣耀的不朽,而这种不朽唯有进入诗歌才能获得。这也是荷马史诗与诗系作品的本质区别。《伊利亚特》着重叙述了三位重要英雄萨尔佩冬、帕特洛克罗斯、赫克托尔之死,并通过帕特洛克罗斯的死来预示阿基琉斯的死。

陈斯一老师认为,三位英雄的形象均改编自诗系传统。萨尔佩冬与赫克托尔的原型应该是失传史诗《埃塞俄比亚英雄》(Aethiopis)中的门农(Memnon)。这部史诗中阿基琉斯vs门农被荷马改编成帕特洛克罗斯vs萨尔佩冬和阿基琉斯vs赫克托尔。门农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特洛伊的同盟,武力高超、德性超迈。他和阿基琉斯一样是女神所生,极其俊美。和忒提斯-佩琉斯-阿基琉斯相比,艾俄斯-提托诺斯-门农是来自东方的更古老神话。这两组神话虽都包含着对神性和人性、不朽和必朽的反思,却彰显了古希腊与近东观念的差异。阿基琉斯杀死门农或许意味着古希腊神话对于近东神话的征服和取代。陈老师还提请我们注意门农的两个荷马分身:萨尔佩冬获得更高的神性血统,赫克托尔则完全不具备神性血统。

陈斯一老师指出,荷马着重描写的三位英雄之死各有特色。其中萨尔佩冬之死是非常重要的一幕。在萨尔佩冬与帕特洛克罗斯对战之前,宙斯想解救他,却被赫拉制止。赫拉认定,英雄的最好归宿不是存活,而是厚葬。荷马用两个经典比喻(松树-造船、狮子-公牛)描述萨尔佩冬之死。这种极其诗化的描写与其他人的死亡对比鲜明。《埃塞俄比亚英雄》中的另两个情节要素:神圣铠甲和命运之秤,则被用在了赫克托尔身上。阿基琉斯刺穿自己的铠甲杀死赫克托尔,这幅铠甲又是赫克托尔杀死帕特洛克罗斯后所夺。三位英雄身穿铠甲的样子极为相似,尤其是阿基琉斯绕特洛伊城追逐赫克托尔一幕。而通过描述赫克托尔死前和平生活的景象,在日常生活场景的烘托下,荷马凸显了死亡让赫克托尔返归本性的主题。
陈老师总结道,这些重要的英雄走向死亡的故事就是《伊利亚特》的质料,而荷马作为创作诗歌的工匠,通过重新编排传统的死亡意象与情节,重组各色英雄的死亡,由此形成不同的相互交织的线索。这样的悲剧诗学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反差性对立。这就仿若亚里士多德和尼采的悲剧诗学,通过模仿实现净化,通过提供狄俄尼索斯的内容并塑造一个阿波罗的框架表达了所谓的悲剧精神。

在评议环节,来自重庆大学哲学系的何祥迪副教授充分肯定了本次讲座的深度和丰富蕴含,他认为该讲座涉及荷马史诗,亚里士多德,尼采,荷马史诗问题等重大内容。何祥迪老师指出,陈老师最重要的创新点在于采用哲学上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解读《伊利亚特》的战士之死(内容,生活)与诗化死亡(形式,诗歌)。何老师还提出一些问题与陈老师商榷。首先他表达了对讲题中涉及的“悲剧诗学”的疑问。他指出,当我们谈论“诗学”时,我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套解释文学性质的理论学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学(poiesis)的原意就是“制作”,而不是说荷马有一套悲剧的理论。因此我们难以想象有一种自觉的悲剧理论的意识来创作悲剧,创作者也不一定有理论。因此,陈老师使用“荷马史诗的悲剧诗学”很大程度上是谈论荷马史诗的创作问题。其次,何祥迪老师探讨了将亚里士多德和尼采放在一起谈论诗学的可行性。他认为,尼采本身反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因为它们用理性(日神精神)的思路去理解悲剧,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创作悲剧,恰恰就埋葬了悲剧精神(酒神精神)。对于荷马史诗是否依据传统或东方题材进行改编,何老师也表达了疑虑,即是否有足够的证据确暴荷马史诗中的这些改编来源的真实性。最后,何老师还提到赫克托尔的僭越在何种意义上理解,以及《伊利亚特》的悲剧诗学阐释能否运用到《奥德赛》本身的问题。
在互动环节,陈斯一老师就何祥迪老师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回应,进一步探讨了亚里士多德和尼采的理论是否相通、荷马是否运用到更古老的材料、赫克托尔的僭越以及《伊利亚特》的解读方式是否能运用到《奥德赛》等问题。最后,陈老师详尽解答了线上网友提出的荷马史诗的真实与虚构、荷马将死亡诗化的动机、《伊利亚特》对死亡的模仿与人类命运的关系、荷马史诗中诸神与命运的关系等问题。主持人罗峰老师在尾声出提议,我们理解荷马史诗需要警惕“分析学派”肢解经典统一性和教育意义的危险,为本次荷马史诗盛宴画上完满的句号。
图文 | 徐颖、罗峰